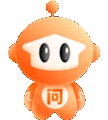川端康成:
岛村仿佛坐上了某种非现实的东西,失去了时间和距离的概念,陷入了迷离恍惚之中,徒然地让它载着自己的身躯奔驰。单调的车轮声,开始听的时候像是女子的絮絮话语。 这话语断断续续,而且相当简短,但它却是女子竭力争取生存的象征。他听了十分难过,以至难以忘怀。然而,对渐渐远去的岛村来说,它现在已经是徒增几许旅愁的遥远的声音了。
大主教:
碎裂化蝶的花窗
被一股月光连结
银丝微撩
金烛轻颤
看那圣母的血泪
鸠羽熬炼的圣咏中
血丝蔓布的香薰里
化作渴望起舞的群蝶
正向龟裂的花瓷
撰写一笺
青灰的邀请函
守墓人:
冷夜寂寥
墨渊无涯
灵车的鼓锣
请与我一同
失声
失声
垂首静听
经纬的哀鸣
伊萨卡:
不曾取下的面具
竟丧在一片桃园
诗人:
伊萨卡
无忧的弗纳斯
乘鹿的狄安娜
恍惚间轻轻踱到我耳旁
紧绷面具的丝带被解开
镜子那头
一个陌生的孩子
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在一片花海的簇拥中
正笑着流泪
伊萨卡踮脚注视滚过的泪珠
轻笑了起来
伊萨卡:
卡尤加湖面的风
是握不住的凄柔
旅人:
新生的脸迎着湖面的风
算得上真实的只有刺痛
伊萨卡
跃起捕风的你
伏下捉影的你
与水鸟交换姓名
和浪纹嬉闹的你
怎么尝得出
掠过湖面的使者眼里
那缕握不住的凄柔
旅人/诗人:
伊萨卡,伊萨卡
你是否明白
你赋予感情的万物
只是从你而出的涟漪
因风而动的枝丫
旅人:
如今我将要转身离开
从流光满溢的波涛里
乘一块补丁驶入迷雾
遥望湖边的金柳
竟丧了转身拭泪的勇气
伊萨卡啊伊萨卡
被禁止带走云彩的我
应该带走什么
伊萨卡:
摆渡自己的漂木
注定一生漂泊
旅人:
带走一个满了泪的小瓶
带回一缕如发般的海草
带走一块湖面起伏的白帆
带回一点床头扰梦的萤火
带回一株内向的薄荷
带走一暮惊慌的小鹿
带回一圈溢彩的光晕
带走一粒泛黄的钟响
旅人:
在所有亲切的可能里
我做了最懦弱的选择
在树荫下,勒忒身前
买下滞销的回忆
伊萨卡
我又如何不知
那如沙回忆的狡猾
伊萨卡:
如沙的回忆
是诸神戏耍旅人的手段
诗人/旅人:
伊萨卡,伊萨卡
无忧的弗纳斯
乘鹿的狄安娜
恍惚间踱到我耳旁
镜子那头
一个熟悉的孩子
一张布满皱纹的脸
在一片勒忒的谎言里
正笑着流泪
旅人:
愿你银丝满头
仍在殿内高歌
家乡的小巷:
遗忘引你探雨巷
绝食的人儿一倚靠
青苔就漫上墙角
辗转昼夜,滴水檐角
木板车来回吟着一个调
星河醉后痴望着月,
噤声编织着梦
可是要给远方
那被旅行的人?
远方的大道:
九岁的孩子莫回首
蒙纱的雨巷口
荷蛙吟出一张通行证
愿你远去,愿你远去
莫沾染了灰烬
吹成一朵风砂
旅人:
天空遣飞鸟向大地
发来贺礼
大地邀树木向天空
挥手致意
海浪
是洋和礁的相拥
黄昏
是夜和日的交融
身处于如此亲密的互动中
人
当退至一旁
家乡的大道:
绝望赶我上街角
恐惧的马儿一奔逃
芍药就开成了惊涛
无眠艳阳,浆硬衣袍
特洛伊回放着泛黄的笑
竹海醒来默念着星
同声谱写着歌
可是要给远方
那被旅行的人?
远方的小巷:
七旬的老翁切留步
烛天的火道上
谪仙舞出一纸驱逐令
何必离去,何必离去
勿阖上了刀伤
点一盏红风灯
旅人:
曾经我还对你抱有一丝病态的希冀
在你不断的逼问下
我选择将其彻底放弃
政治家:
曾 以为
无论阳光如何毒辣
只要汪洋依在
溪河便永不干枯
又 岂知
纵使汪洋依在
无边浩瀚
但其吝施恩惠
弃众儿女于不顾
于是烈日当头
江河湖泊
转瞬即亡
何其不幸
牧师:
吾 正处将亡之溪
死期将至
众鱼却相顾而言
“瀚海莫测高深
吾辈岂能猜测其旨?”
我也不会质问大海
不 因畏惧
只 因
汪洋大海,浩瀚无边
岂能听见
一只将死之鱼的哀鸣?
旅人:
淡风吻起的涟漪
晕开灯芯的鹅黄
绿林低吟的凄凄
夏虫最后的彷徨
众人:
要么伟大,要么死亡
旅人:
天神搅动的云雨
剪乱泼洒的金轨
世间最贵的香薰
老翁兜中的烟草
众人:
归家吧,归家吧
旅人:
被晨褪去的夜色
护拥着恋人的梦
雨打芭蕉的咏叙
小鹿蹦跳的腔胸
众人:
爱难道是同世界离开的事吗?
旅人:
刀匠上扬的吆喝
催醒迷茫的苍穹
流归大海的溪河
伴我归家的脚踪
众人:
归家罢,归家罢
摆渡人:
伴 暮鼓晨钟起卧
乘 黄蜂紫燕来往
览遍半溪流水 千树落红
听过春日莺恰 秋天雁雍
又哪知
不过徒揽了一蓑烟雨 添两鬓霜华
七弦的绿绮
已被尘虑打上了结
沈从文:
他的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
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
揉进了他的生活里时,
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
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
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若有多少不同处,
不过是这些人更真切一点
局外人:
瞧,请瞧,猪狗牛羊向我叫嚷着“人性呀人性!”,那用那双眸子看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分。怡然照旧,持一粒石灰思考无限,看一截脐带探索死亡。我本无鼻无耳,无指无目,对自己浑浊的存在有确实的证据。而如今,却被加上这可笑的装饰,被与我相似的幻影蒙蔽了双眼,所以我的选择,怎可能,不黑暗?自称为人的假象,请向我展示你们的踪影。摧残我,唾骂我,或与我相爱,好在泯灭归回混沌的自我前,能够欺哄自己说,你们与我一样。无谓无用无味无色,被眼白淹没的黑夜起,鬼神的啸叫就只让我感到亲近。
旅人:
你是谁?谁是你?
局外人:
含入光就吐出银河,吞噬虚空就呕出苍穹,捧住一双盈盈的玉手,定不能收获什么。徒有一支剪下清风的燕尾,一柄网住黎明的银杏。芍药绽放的惊涛下,孤倚桥洞内壁,哀悼三分蒙茸。门前巧朴的木凰,已生出一翼曜灼。总有一天,当地精把我分解,空灵将你接去,三叩九拜的大礼被打断,脚下一滑跌回同一个万物的子宫。宇宙的鼎炉里你将无法拒绝,而我会转身,跃入燃烧万年的文火。在那之前,我的爱,何不一同逆流遁入柏油上倒灌涌来的光,麋鹿角间铺一榻灯芯草,剪红心和黑桃堆叠起一夜无眠,谁不明白装睡的额头比睡着的脸更安详?春风廉幕的日子,三对浴波白鸥的湖面旁,起承,转合,七弦的绿琦被尘虑打上了结,白蓑内镶金的烟雨,挤过砖缝溜向芦苇塘。若你撩开额前镀银的散发,我就接一壶檐上注下的雨,泡一沽拾来的玉兰花。静听!雀跃的南风,已在门前留下了一洼汪洋。
旅人:
我是谁,谁是我。
局外人:
明白了吗?黎明的苦楚,黄昏的欢愉,夜与日交合的癫狂,都是你我的倒影。俄狄浦斯和西西弗,小市民和丑角,终究还是四选一。打破反复昨日的节期,成了下一个年轮,不如引余晖打上紫浪的泡沫,采一朵琉璃,点一海灯笼,只是烛光前的泪少几颗,炊烟后的笑减几何。十载,百年。精通幽默之人必遭囚禁,其不过误看人人皆知的天机,秉一份遭诅咒的聪慧,叩破现实与梦间的油幢。尽管,遭宇宙之忿怒,受万象之凌辱,芥子乃为本性所迫,依依拔生,撬动巨石。如是我言: 人于现实认梦为虚幻,或为梦里无味,或为无质,或为无声。然则,现实不也同有盲人,哑巴吗?以此说来,觉得现实虚幻的梦中人有什么过错?
旅人:
你是我,我是你……
局外人:
我可以承鬼诞离奇的罚,却断不担这莫须有的罪,“恣肆”的佳名太奢侈,我受不起。若是要让你们明白,人生从未如梦,人生乃梦,梦是人生的道理。我只有利用死亡那荒诞的说服力,让世界听见我的歌。何惧死亡?只怕死在梦里的小孩之前,给他无梦的余生,不情愿,不值得。就这样,凝视走马灯的旋转来回,怀揣着一块破怀表,痴了,醉了,分不清自己是月亮,还是被月光照耀的人。到头来提一盏白日,十七次渡河,十七次途穷,十七次摆渡,十七次大哭而返。这一次,这一次,我愿就地而眠。
旅人:
我不是你!你不是我!
引路人:
他的崇高灵魂与他想要拯救现实的心是对他最大的诅咒。崇高的灵魂让他排斥达芬奇繁杂的研究以及拉斐尔优雅的臆想、排斥佛罗伦萨、友谊、转瞬即逝的爱情与一切之所能见。然而他那更高贵的、英雄式的心却促使他日以继夜地用画笔、颜料和凿子不断地传递崇高与激情。若说安吉利柯预示了拉斐尔的出现,那么马萨乔一定预示着他的出现。诚然,艺术家之作品皆有自画像之本质,马萨乔的作品具有雕刻般的光影体现,最重要的是其作品如雅各布的雕塑般光滑且自然的表面下充满了坚实的内在力量和狂热的情绪。他笔下的作品亦如此,只是更多的,是其矛盾的悲剧的载体。
旅人:
他是谁,谁是他。
引路人:
他在天国与深渊见上下飘动。他飞升而上成为挥动着身体的基督,又直落而下成了挥动木桨的判官;他在半空中惊惧地遮盖面孔,但一只眼却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在新生的圣巴塞罗缪和他手中的皮囊间来回折返而疲倦不堪。他无垠的激情使周围的一切有限,大理石的大小、人体肌肉的构成、画面的大小亦或是透视法都成了他的限制。为了突破限制,他尽全力地将人体在韧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痛苦地扭曲。美即自由,他在自由的四年里独自面对心中的崇高和幽暗深处的上帝,独自经历从亚当到基督的痛苦转变。他向人们展示了其永恒如星辰般的壮阔热情。大理石在他的内心世界面前显得羸弱不堪,顷刻间就在其热情中灰飞烟灭。他只能将其热情极力内敛、压缩于石料中。偶然中亦有必然。最为受限的雕塑成了他选择的,对其无限激情的主要表达方式,何尝不是其又一重悲剧呢。
旅人:
我是他!他是我!
引路人:
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容忍着这个怪胎,而这个怪胎何尝不是在容忍着她们?米开朗基罗所做的工作早已具有哲学性质,修改一句黑格尔描写哲学性质的话来描述这种性质:他把存在于他本质里的,那种超世俗、超自然世界才具有的那种明晰的热情注入到那以混沌和模糊为意义旨归的此岸世界里。一般人的官能知觉深深地扎根于世俗世界内,达芬奇是这种状态的极致,而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两个例外。然而不同点在于拉斐尔享受这样的“离群”,而米开朗基罗则试图在这个立场上与现实争斗。所以,不管文艺复兴如何伟大,米开朗基罗依旧不属于文艺复兴这个时代,且不属于任何时代。就像哈姆雷特不属于,梵高亦不属于一样。哈姆雷特不断与时代周旋,在最后的失败中忏悔;梵高将这样的争斗个人化,并为自己打开了一条出路。而米开朗基罗则坚定地投入斗争中,成为斗争的本体,他斗争的历史被他自己忠实地记录下来,他忍受争斗带来的无尽痛苦,而想要抓住重重矛盾间的瞬间和谐,死亡是他最后的胜利。其作品将永远在拉菲尔无关紧要的和谐和达芬奇五花八门的哑谜里,使无数自认为理解了他部分热情与悲剧的人仰望落泪。
旅人:
我终究不是他,他终究不是我。
摆渡人:
孩子,你可明白,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对于想要超越死亡的人来说,经历了千年的挣扎后,“有限的人若要战胜死亡,则必须要除自己身体意外的,具有无限之本质的助力。”的道理已经人尽皆知。因此有人直接以宗教内的另一个无限人格来从本质上改变自我的有限性,而又有不满于此的一部分人借助“艺术”这个无人格的经验概念来作为自身生命的延展方式。这个举动无疑大胆且悲壮,因为他不提供任何书面的信条和保证。“不朽”永远是历史的仇敌。渺小的事物自然被历史摧毁,然而残酷之处却在于有无比伟大美好的成就因为某种偶然依旧被时间埋葬。然而,即使遗留下来的那一部分如何地稀少,却依旧能够证明艺术的伟大和永生。
旅人: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摆渡人:
嘘,噤声!让我们我们伫立在断臂的维纳斯面前,想象阿历山德罗生命的优美与清灵。即使是像无首的胜利女神,爱琴海旁的无面人,复活岛的巨像这样的无主之作,观者依旧可以感知作品背后那坚实而伟大的存在。然而物质是有限的,难道艺术终将屈服于物质的脆弱,与媒介一同崩坏吗?当米开朗基罗从阿格桑德罗斯的《拉奥孔》内汲取灵感,丁托列托又将“米开朗基罗”的形象作为志愿,委拉斯凯兹前往意大利临摹丁托列托的作品,弗朗西斯·培根,马奈,毕加索,达利又从委拉斯凯兹的作品里获取灵感时,阿格桑德罗斯的生命已经以几十种不同的方式延续。在阿格桑德罗斯之前,必有某个不知名的艺术家对其施以影响,而他的生命也同他被引导者们的生命一起,至今仍在延展。这样的现象,在我所写过的,像“奥林匹斯题材”、“维纳斯形象”、“坠落概念”这些艺术史上下无数通用的艺术符号里,得以证明。
旅人: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摆渡人:
你再看我们在肖维洞穴里打着火把作画,在苏拉威西石窟内按下手印,在金沙江旁锻造金箔的祖先,通过他们对自己生命的表现,如何将自己的生命记号烙进了后代的血液里。因此即使我们看不到两者之间的清晰联系,但在洞穴里的火影摇曳与用火作画,信奉炼金术的克莱因之内,爱琴海石像和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超然之间,依旧可以瞧见藏在血液里的某种渴望和冲动。正是这样的不屈在无形之中鼓舞一个艺术家在黄房子的贫困潦倒或红磨坊的纸醉金迷里完成自己的生命。“由此即可证明艺术不朽,艺术永生”
旅人:
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摆渡人:
不,你还没有。“不朽”永远是历史的仇敌,因为艺术令人生畏的不朽,其被不同的势力从个人手中争来夺去,这些势力将艺术奴役、扭曲,逼迫其为一个单独的个体,为某种意识形态效力。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被摧毁。 在罗斯金的时代,夺去艺术的是“大批民众像燃料一样被送去燃烧工程的烟囱,他们的精力每天都浪费在织物的纯度上,或者被线条的精确所折磨。” 的工业化批量生产所带来的,人性中对美之渴望的麻木。而在沈从文所处的年代,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从世界起初就根植在我们血液里的热情被切断了,加上对宗教的限制,人追求永恒的可能性因此归之于零。这种情况下还想要追求永恒的生命太过渺小,以至于成了滑稽的存在,要么选择荒诞地装疯,要么选择悲壮地自杀。
旅人:
我拒绝!我拒绝!
摆渡人:
米开朗基罗留下的原因在于他需要将自己内在生命矛盾通过载体表现出来,而沈从文则肩负民族兴衰沉浮之忧思,看透人类走向的洞察和无法将其挽回的卑微命运。如果说米开朗基罗的诅咒是他个体灵魂的伟大的话,那么沈从文的诅咒还要加上令人痛苦的洞察力。
旅人:
我不承认!我不承认!
摆渡人:
看透了“‘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诺诺者日有增,而谔谔者日有减” 的现状,被自己决然的本性所逼迫去成为那个孤独的谔谔者。“洞察力即造成了你的烦恼,又消耗了你的胜利。” 何其可笑,你到头来依旧是装疯或自杀。
旅人:
Eureka!Eureka!
后记:
这是一次尝试,以一首我在异国游学三月的经历所写下的诗为主体,再从十七年生命的不同阶段选取了诗句,回忆当时的生命状态赋予了不同的角色穿插其中。虽然混乱了些,但未免不能瞧见字句间隐含的时光。诗是一个生产梦幻的国度,它可以阻止人在过去中消失。这一次前往异国游学的经历,也就是我十七岁生日,是我人生的一个节点。没有人可以永远乘船,在船票售空的情况下,人只能摆渡自己。而十七岁的我就好像一个摆渡自己的摆渡人,从童年启航,经历了亲情的庇佑,友情的羁绊,爱情的挫折,到了至今未知的另外一头。但同时在我的生命中也遇到了两位“引路人”和“摆渡人”,所以我在末尾讲述了我如何通过两位 “摆渡人”和“引路人”,也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沈从文的影响找到了现在的自我,不再成为一个漂泊的旅人首尾选自川端康成《雪国》和沈从文《边城》,我所经历的摆渡,正是从那一个遥远的雪国,回到了属于自己的边城。总体分为两部分,诗歌部分是以一个身处其中的剧中人,通过十七年头的摆渡过程中自己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来反映自己在不同阶段的所思所想。而相对理性的散文阶段则是站在一个已经到达对岸的人的角度,回望过去,发出一句忏悔,一篇声讨,一纸遗言,渡过了这条河,给过去立下墓志铭,该开始新的跋涉了。
作者:许思为 所在学校:维理达学院 指导老师:查常平
本文系“摆渡人”杯全国高中生征文大赛百强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① 凡本站注明“稿件来源:中国教育在线”的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稿件,版权均属本网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本网协议授权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表。已经本站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下载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中国教育在线”,违者本站将依法追究责任。
② 本站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站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在两周内速来电或来函联系。







 中国教育在线
中国教育在线